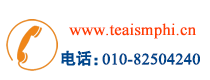陶德臣:英国褔钧对华茶业经济间谍活动述论
声明:本站所有原创文章均为作者投稿版权文章,转载请务必注明出处“中国人民大学茶道哲学研究所(www.teaismphi.cn)” 。个人投稿文章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文责原作者自负,敬请读者诸君自行判断。
编者按:本文作者为陆军工程大学政治工作系教授,研究方向为茶业经济和文化史。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视野下的西南茶马古道文献资料整理与遗产保护研究”[20&ZD229]阶段性成果,全文刊登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史评论》2024年第1辑。作者授权在人大茶哲所新媒体全文推送,以飨读者.
英国褔钧对华茶业经济间谍活动述论
陶德臣
摘 要:19世纪上半期,英国福钧对华茶业经济间谍活动是一场十足的盗窃活动。他实施这一活动的针对性极强,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服务于英国垄断茶叶利益、培植茶叶产业、控制世界贸易这三大目标。英国福钧对华茶业经济间谍活动涉及面广,包含内容多,持续时间长,主要内容是向中国窃取英国发展茶业必不可少的种制知识和技术、茶籽茶苗茶树、茶叶种制技工等方面,以便让英国建立起完全独立于中国的殖民地茶业经济。经过不懈努力,英国福钧对华茶业经济间谍取得了相当成功,并对世界茶产业造成了深远影响,最终促成了英国殖民地茶业的迅速崛起,改变了世界茶叶生产和贸易的原有格局。它使中国数千来积累下来的茶业技术完全失密,结束了中国茶叶垄断世界市场的局面,开启了近代中国茶业衰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福钧对华茶业经济间谍活动还增加了中国社会民生改善的困难程度。近代中国茶利减少,茶农生活困苦,茶商处境艰难,中国社会民生问题突显,就是这一间谍活动的恶劣影响。
关键词:英国;福钧;中国;茶业经济;间谍
罗伯特·福钧(Rorbert Fortune,又译作罗伯特·福琼、罗伯特·复庆、罗伯特·福顿、罗伯特·福特尼,1812-1880年),英国苏格兰人,植物学家。1842-1845年、1848-1851年、1853-1856年,他3次潜入中国内陆茶区,非法从事植物采集活动,公然“在中国鼻子底下窃取中国的茶叶机密”[①],将中国茶树、茶籽与制茶工艺等珍贵财富偷偷输出,引进到英国东印度公司开设在喜马拉雅山麓的茶园,结束了中国茶对世界市场的垄断,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损失。1996年,英国茶道爱好者、纪录影片制作人、法学家威利·佩雷尔施认真阅读了福钧的手记《茶叶和鲜花之路》后,与同为电影工作者的姐姐黛安娜·佩雷尔施因以及另一位合作者一起开始研究。历时4年的研究证明,“福钧当年的冒险活动乃是一种经济间谍活动。”[②]《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一书的作者也认为:“但若要茶叶成功落户印度,英国需要从最好的茶树上采集最健康的样本、成千上万的茶种以及中国顶尖茶匠传承了千百年的工艺。完成这个任务的人必须是一个植物猎人、一个园艺学家、一个窃贼、一个间谍。这个担负着大英帝国希望之人,名为罗伯特·福钧。”[③]可见,福钧就是彻头彻尾的经济窃贼、间谍。什么叫间谍?“今指由异国情报机关派遣或指使,窃取、刺探、传送机密情报,或进行颠覆、破坏等活动的人员。包括外国人,也包括本国人。”[④]经济间谍是指受别国情报部门派遣或指使,窃取、刺探、传送经济机密情报的人员。英国对华茶业经济间谍活动由来已久,它以窃取茶业经济机密为目标,包括茶叶知识和制茶技术、茶籽茶苗茶树、茶业技术工人等关键内容。在这一长期茶业经济技术窃取活动中,罗伯特·福钧发挥的作用非同寻常。学术界对福钧的茶业经济间谍活动已有所研究[⑤],但从单篇文章加以专门讨论的成果不多,有必要继续深化研究。下面从长远目标、主要内容、恶劣影响三大方面揭示福钧对华茶业经济间谍活动。
一、福钧对华茶业经济间谍活动的长远目标
“茶起源于中国,盛行于世界。”[⑥]中国是茶的祖国,中华民族的祖先最早发现茶树,很早就开始了对茶的利用,进行了茶树栽培、茶叶制造,开展了茶叶贸易。直至19世纪30年代前,中国仍然是世界茶叶市场的唯一提供者。“15年前(即1861年——引者注)中国垄断着茶叶的生产,当时印度阿萨姆的茶叶种植正在萌芽时期”[⑦]。20世纪初,孙中山也说:“前此中国曾为以茶叶供给全世界之唯一国家,今则中国茶叶商业已为印度、日本所夺。”[⑧]作为世界最大茶叶消费国的英国,19世纪最多时一年从中国进口茶叶达100万担以上。但是,英国殖民地印度、锡兰茶业发展后,首先在英国市场上成为中国茶叶的劲敌。1866年,英国人消费的所有茶叶中,只有4%来自印度,到了1903年,这个比率上升至59%。这一不幸局面的产生必须讲到一个关键性的人、一件关键性的事,这就是英国福钧对华茶业经济间谍活动。福钧是极力鼓吹在印度植茶的狂热分子,他露骨地声称:“在印度成功种植茶树所能带来的好处将是巨大的。”[⑨]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他必须从中国秘密取得发展茶业必不可少的技术。他实施的茶业经济间谍活动目标十分明确。“通过对喜马拉雅山茶的一系列实验,东印度公司的一系列目标变得简短而明确:寻找中国的‘香味混合剂’、中国最好的茶叶、中国的茶叶制作知识,还有中国籍的制茶工和中式制茶工具”[⑩]。这是短期目标,也是福钧茶业经济间谍活动的主要内容,而长远目标则是为英国及东印度公司垄断茶叶利益、培植茶叶产业、控制世界贸易服务。
(一)垄断茶叶利益
英国政府和东印度公司都从茶叶贸易中取得了巨大利益。茶叶贸易兴盛首先使英国政府获利丰厚。17世纪中期,英国已有茶叶出售,相关广告也公开宣传饮茶。当时茶价很贵,“此后,中国茶叶很快就成为英国一种时髦的饮料。”[11]茶叶消费数量水涨船高,为征收茶税创造了条件。英国茶税首创于斯图加特王朝。1660年,查理二世时,议院开会,第一个议案就是茶税议案。议案确定了茶叶奢侈品的地位,征税税率为每加仑8便士,茶税成了海关关税的重要来源[12]。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茶税税额从基本稳定变为不断上涨,涨幅很大。1692年,英国茶叶进口关税从中国进价的10%减为价格的5%,1699年恢复到10%。嗣后,茶税税率大增,1768-1772年为64%,1773-1777年竟达106%,1778年后有所下降,为100%,1783年又增至114%。18世纪中叶,英国由于财政困难,茶税成为税收大宗来源,1784年,茶税甚至高达190%。1711-1810年,茶税税率不等,从12.5%至200%,英国政府取得的茶税达到7700万英镑,超过1757年所负国债金额。茶税的增加比较迅速,1793年只有60万英镑,1833年达到330万英镑。为了解决私茶问题,英国政府采取大幅降低茶税的办法。1784年9月1日,实施“抵达法案”,茶税从高达190%降到12.5%,岁入不足部分以窗税弥补。由于茶叶走私得以杜绝,茶叶正常输入量大增,英国收入也因之大增,全年茶税收入约70万英镑[13]。从1784年9月1日至1797年,英国政府获得的茶税共为4832189英镑,年均40268.41英镑。从1784年9月到1795年3月,税率保持上升趋势,1784年税率为12镑10先令/百磅,1795年3月至1796年3月,茶税上升至20镑/百磅。1797年3月,售价2先令6便士/磅以上的茶叶税率为30英磅/百磅[14]。可见,茶税保持上升趋势。1806年,茶税税率接近100%,到1833年止,“一直停留在100%而无重大的调整”,“英国政府从茶叶获得的利润几乎和东印度公司获得的一样多”[15]。上文已提到,1793年,英国茶叶总收益是60万英镑,1833年激增至330万英镑,1846年,征茶税500万英磅[16],1905年,英国茶叶进口税竟高达800余万镑[17]。可见,茶叶贸易给英国政府带来了极其丰厚的利益,当然就不难理解“政府是非常关心对华贸易的性质和未来的”[18]这一情况了。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茶叶贸易中同样获得了丰厚利益。早在1704年,东印度公司在中国市场花2先令/磅购买的上等好茶,在英国市场售出时卖出了16先令/磅的高价。第二年,英国“肯特”号商船来广州载茶470担,价值1.4万两白银,折合10英镑/担不到,如以售价16先令/磅计,则可得2132.8先令/担,等于106.46英镑/担,售价在10倍以上[19]。据统计,1711-1759年,东印度公司账面利润高达18216144英镑,年均371758英镑[20]。1793-1810年间,“所有运往英国茶叶的‘进货原则’是27157066镑,而销售价格是55160230镑,这指明了所加上的费用和利润为百分之一百零三”[21],年均销售收入为1647244.9英镑。1830年,英国下院也认为东印度公司茶叶利润很高,“每年一百万镑至一百五十万镑不等”[22]。实际上,这个估计数字太低了。有材料显示:“1712年,茶叶的总进口量是1500000磅”,一个世纪以后,“东印度公司销售收入达3500000英镑,进口的茶叶的价值比其他所有货物加在一起的总价值少不了多少。”[23]东印度公司垄断的最后几年,茶叶提供了“东印度公司的全部利润。”[24]此时期,英国国库得到的茶税年达330万英镑,如果考虑到“英国政府从茶叶中获得的利润几乎和东印度公司获得的一样多”[25]这一事实,东印度公司的利润起码也不会少于年均330万英镑。这一数量几乎是18世纪50年代的10倍。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权被取消后,茶利得来的丰厚财源并未干涸,甚至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前线军事指挥官在战争状态下还想方设法使“参加这项投机生意的‘朋友们’获得厚利。”[26]之所以发生这样奇葩的事件,主要是茶利丰厚太有诱惑力了的缘故。
正因为茶利这么丰厚,诱使英国政府和商人企图将这一利益悉数收入囊中。中国是茶的祖国,“茶叶只能从中国取得”[27],这就是铁定的事实。离开中国茶供给,世界茶叶消费就无来源。虽然当时日本也有少量茶叶生产与出口,但其地位和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同时,英国人又越来越离不开茶,茶早已融入英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是茶的故乡,英国则将下午茶文化发挥到极致。”[28]这两大压力使英国无时无刻都要依赖于中国茶。“除了利润的考虑而外,有一种主要的中国产品而在其他地方所买不到的东西(指茶——引者)日益变为英国各级社会人士生活中的必需品”[29],这就是令他们为之神往的中国茶。为了打破中国对茶的世界性垄断,满足自身消费,攫取更多利益,英国定下决心在殖民地种茶。为了尽快实现这一野心,英国指示1792年访问中国的使臣马戛尔尼尽其可能搜集茶叶情报、茶籽、茶树,并迫不及待地说:“茶之数量及价值均极大。此物如能在印度本公司领土内种植,至惬下怀,此事吾人极力祈君注意。”[30]不过,英国人拥有的茶叶知识十分有限,对茶叶种植、生产、制造可谓一窍不通,他们马上想到的是只有采取十分卑劣的方法,不择手段对中国茶业技术进行野蛮盗取了。
(二)培植茶叶产业
中华民族在长期利用野生茶的过程中,形成了人工植茶、茶叶采制及销售和消费于一体的茶业经济。古人在长期从事茶叶生产的实践活动中,创造和积累了极为丰富的茶园开垦管理、茶树选种育种、茶苗茶树移栽、茶叶采制储藏等一系列成熟技术。这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它体现在众多茶书茶著中。要培植发展茶业,这些茶业知识、技术必不可少。茶苗茶籽是发展茶业的基础,茶业技术是发展茶业的核心,茶业工人是发展茶业的关键,这三大因素缺一不可。离开了这三大要素,尤其是没有茶业技术和相关专门人才,茶业不但难以产生,更谈不上发展。中国茶业早在唐宋时期已趋繁荣,陆羽《茶经》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茶叶专著,将茶业推进到技术的发展阶段,为种茶、采茶、制茶、藏茶、饮茶提供了指导。明清时期,茶业技术更见发达。然而,包括英国人在内的西方人到16世纪才接触到茶知识,相当长时间内,他们的茶知识很贫乏,更不要说知道种茶、制茶知识和技能了,就凭这种状况,他们是不可能培植出茶业来的。
17世纪以后,当中西贸易发展后,茶叶在中英贸易的地位不断上升。18世纪以前,英国从中国进口的茶叶还不多,1664-1720年,英国共从中国进口茶叶3709843磅,折合27830.78担。1717年,茶叶成为英国自华输出的首要商品。18世纪20年代以后,茶叶成为中西贸易的核心商品,英国进口的中国茶叶数量有了较大幅度增长。从1721到1755年,英国共进口中国茶叶51381382磅[31],折合385456.7291担。自1756至1840年,进口中国茶叶14107916担。1721至1840年,英国共进口中国茶14493373担。
为了获取中国茶叶,满足国内消费,并向他国进行转口贸易,英国极不情愿每年向中国输入大量白银。17世纪开始,白银占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出口货值比重已经很高,18世纪中期在90%以上。1708至1712年,英国每年对华出口货值为5000镑,白银50000镑,白银占90.9%,1730年,来华东印度公司5艘商船载白银582112两,货值13711两,白银占97.7%。1731年,来华商船3艘,载白银65547两,货值14010两,白银占97.9%。1708至1760年,东印度公司向中国输入白银占对华出口总值87.5%[32]。1758至1762年,东公司对华出口货值174000两,白银219000两,白银占55.7%,1766至1770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输出总值中白银约占50%,1795至1799年这一比重下降至13%。这主要是鸦片输入的恶果。由于对华出口总值高达5373015两,白银输出数量年均仍高达739994两。1823年,东印度公司对华白银输出659998两。1760至1823年,东印度公司对华白银输出233121032两。根据学者估算,从1700至1823年,东印度公司总共输入中国的白银高达53875032两[33]。
如果再加上英国输入鸦片因而抵销的白银数量,则价值更大。不管怎样,鸦片成为对华输出主要货物以前,英国不得不每年向中国大量输入白银才能平衡贸易逆差。无论如何,这是英国极不情愿看到的局面。为此,一方面,英国无耻地向中国输入鸦片,以抵销由于输出茶叶造成的白银外流;另一方面,计划在其殖民地培植茶业,以满足日益增加的庞大消费需求,并确保将巨额茶利建立在更加牢固可靠的基础上。“茶叶种植当然是排在最重要的位置。”[34]其实,“英人早思於属国择选土地,宜於艺茶者植之,以省费利国。”[35]英人认为“茶叶销用极广,故我等於各地尽心栽种,欲敌中国独行之买卖。”[36]印度被认为是英国殖民地植茶的最好地方。1847年9月20日,英国印度总督哈丁在一封致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的信中,流露出对在喜马拉雅种茶的热切期待。他说:“我经过深思熟虑后,觉得我们如果种植这种(喜马拉雅)茶叶的话,很可能只要短短几年时间,就能为我们的国家开辟一座收益极其可观的金矿。我们在喜马拉雅山推广这种茶叶的种植,甚至无限扩大它的种植面积都没有什么明显的困难。我敢打包票,在并不遥远的将来,这种茶叶的产量不光可以满足印度市场可能出现的巨大需求,而且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将足以与中国茶叶在欧洲市场上竞争。有了它,英国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那个外邦在这种生活必需品上的严密控制。”[37]但“一直以来,中华帝国几乎完全垄断了这种‘清澄碧玉’的所有产销环节:种植、采摘、加工、炒制及其他加工方式、批发、出口……一切一切,皆由此一国独享。”[38]虽然,“茶树很容易移栽。问题是来自中国人的阻力。外国人不被允许进入这个国家,即使进入,也只限于广东一隅。”[39]特别是中国皇帝“禁止外国人访问任何一处茶叶种植区。”[40]因为,“制茶的配方在这个戒备森严的国家可是机密。”[41]《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的作者萨拉·罗斯也承认:“茶叶符合知识产权的全部定义:它是一种商业价值极高的产品;制茶需遵循一整套受中国严密保护的准则和中国式的独特程序;这套完善的准则和程序是中国茶叶对其竞争对手保持巨大优势的秘密所在。”[42]发展茶业经济,对英国来说完全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挑战无处不在,茶苗茶籽茶树、茶叶采制技术、茶业技术工人都必须从中国才能得到。另外,“与这个问题(指茶叶加工——引者)相关的第一手资料,甚至第二手资料在大不列颠帝国统治范围内都难觅其踪。”[43]为了保护民族利益,清政府严格禁止茶业机密出口和向国外泄露。对于清政府这一维护国家利益完全正当的规定,英国心知肚明,说:“东印度公司很清楚,把茶种和茶叶技术带出中国很难办到,而通过正常外交途径解决更是痴心妄想。”时任英国驻上海领事卢瑟福·阿尔科克对英国印度总督哈丁提出告诫:“总督阁下,事实无疑将自证,中国人可能带着强烈的警惕心在密切关注我对于茶种或茶树的要求,任何关于企图获取茶种、试图劝诱中国种茶专家和熟练制茶工出国前往印度,并对那里的工人进行培训的努力都将不可避免地以失败告终。”换句话说,“如果东印度公司想要把中国茶种和制茶技术弄到印度的种植园的话,那只能靠偷了。”[44]于是,英国完全置中国国家利益于一边,长期采用非法手段大肆进行窃取。1848年初,“东印度公司制订出了一个纯属商业间谍活动性质的计划,一旦公司的阴谋得逞,那么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跨国股份有限公司将成为这场人类有史以来最重大的商业机密盗窃案的幕后黑手。”[45]
(三)控制世界贸易
茶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发达国家控制世界的重要工具。正因为茶叶有如此巨大功能与作用,因而尤为英国所重视。“当喝茶变成英国以及它那广袤殖民地人们的生活必需时,大规模的、成本低廉的茶叶生产就不再是一件普普通通的事情了。”[46]18世纪60年代前,欧洲消费的茶叶大多数还是由荷兰供应,荷兰一直是中国茶叶最大输入国,首都鹿特丹是国际茶叶贸易中心。荷兰对世界茶市的垄断引起茶叶贸易后起之秀英国激烈竞争。“但是在十八世纪的时候,为了国内制造家的利益”,英国东印度公司“被夺去了从印度纺织品进口中赚钱的机会,于是它就将它的整个生意转到中国茶叶的进口上”[47]。在经过三次英荷战争及英国竞争打击下,1795年后,荷兰被迫基本退出中国茶叶市场,英国取代荷兰成为中国最大茶叶贸易国。18世纪50年代前,英国输出的茶叶占中国茶叶外销总量30%以上,18世纪80年代后增至50%以上。19世纪初,英国几乎将所有欧洲国家排挤出中国茶叶市场,只有美国能分享约20%的市场份额。英国从中国年输出茶叶数量由18世纪30年代中期前的数千担增至万担以上,18世纪40年代后期年均达2万担,1785年起超过10万担,鸦片战争前已达30余万担。19世纪70年代前,中国茶叶60%以上输往英国。
英国取得垄断中国茶叶对外贸易这一重要地位以后,伦敦摇身一变,取代荷兰首都鹿特丹,变成为国际茶叶贸易中心,“欧洲茶市,伦敦实为中心”[48]。英国利用掌控世界茶叶资源的有利条件,将茶运往世界各地进行销售。但是,由于“丝毫没有意识到茶叶是中华帝国负责生产的。中国人采摘茶叶、烘焙、混合后,再以一个包含利润的价格卖给英国。”等他们明白到这一点后,不但极为恼火,也极为不甘。他们知道:“中国利用对这种饮品的完全控制,统治了英国人的品位达两个世纪之久。”“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愈发厌倦与那些贪得无厌的中间人打交道,也早已不愿在茶叶销售利润上被那些可恶的中国人分走哪怕一小杯羹。”对于“小小的茶叶就这样成了地球上依旧敢与大英帝国叫板的一个大国的象征”[49],他们极表不满。他们从完全控制茶叶生产、茶叶贸易的目的出发,决定发展殖民地茶业。“虽然东印度公司的态度不积极,但是一些经销商和企业家越来越认为,中国不应该独占这种世界上利润最为丰厚的,而且利润一年比一年高的商品的所有好处。”[50]为了更好地实施这种控制,英国不惜采取间谍手段,窃取中国茶业情报,发展殖民地茶业,从而牢牢掌握世界茶业。他们的最终追求目标是:“印度能够生产足够的茶叶数量,不仅可满足英国的需求,而且可满足全世界的需求”[51]。看来野心着实不小。
二、福钧对华茶业经济间谍活动的主要内容
中国是茶叶原产地,世界上所有茶业技术都是中国人创造的。“英国之人,嗜茶者众。向者茶利为中国所擅,虽英人据有印度鸦片之利,流毒中国,犹不足以敌其茶也。嗣而有人建议创设种茶于印度,以弥利源。既有成效,因复种之锡兰,不意蒸蒸日上,转使中国之茶,黯然无色。”[52]但“中国人一直不明白自己的茶叶机密是怎样泄露出去的”,现在人们终于搞清楚了,这一恶果其实与英国人福钧长期“在中国人鼻子底下窃取中国的茶叶机密”[53]有直接关系。东印度公司在合同中明确训示福钧的盗取任务:“除了从最好的产茶区搜集一批茶树树苗和茶种运往印度外,你还必须充分利用每一个机会,掌握中国人手上有关茶叶作物种植与茶叶制作的信息,以及那些在印度被委任主管茶园的人应该被(培训)掌握的技巧。”[54]福钧明白,为了让东印度公司的茶叶种植园得以启动,“他所要带回的几千株茶树苗、成千乃至上万颗茶种,外加高度专业化的中国茶叶种植加工技术将至关重要。他必须用某种方式来说服中国最好的茶叶工厂的工人离开祖国随他一起前往印度。”[55]这也是他对华茶业经济间谍活动的主要内容。
(一)窃取茶业种制知识和技术
茶业种制知识和技术是两个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方面。茶业知识的掌握是茶叶种制技术的基础,茶叶种制技术是茶业知识的体现。福钧的茶业经济间谍活动着眼于掌握茶业必要知识,同时也对茶业技术进行窃取。
一是茶业种制知识。众所周知,茶树及相关知识都来源于中国。虽然到19世纪40年代福琼访问中国前,西方国家对茶的了解已有数百年,但对茶树的了解及相关知识的把握还远远不够。福琼3次深入中国茶区,尤其是第二次亲赴徽州绿茶区、武夷山红茶区这些中国最著名的茶区,对茶树本身及生长环境等有了近距离的了解,通过观察、询问、参观等各种途径和方式,福琼掌握了大量茶树茶籽及相关知识。这些知识是一笔弥足珍贵的宝贵财富,对印度茶业的试验及发展起了极大推动作用。
印度植茶业的起步与发展首先要输入种茶知识,对茶树特性及生长环境、规律知识的把握则是关键一环。中国种茶知识的持续传入,主要是1834年印度成立茶叶委员会之后的事。此年,该会秘书戈登来中国,非法调查栽茶制茶方法。“尽管前一个茶叶猎人(指戈登——引者)成功地将一堆各色各样、品种混杂的次等茶叶作物带到了印度,然而这是毫无意义的。”[56]缺少茶业知识,制出的茶叶品质也差。1842-1845年,“通过第一次中国之行,福钧学到了比任何其他西方人都多的关于茶叶种植的知识。”他的“《华北各省三年漫游记》一书有整整两章是专门描写他如何观察那里的茶叶作物的生长、收获及制作过程。福钧甚至将茶树样本带回了英国的植物园,这些移植到温室中的灌木被证明极具研究价值,但根本无法提供任何关于茶叶制作工艺方面的详细信息。”[57]1848年,福钧经精心乔装打扮,第二次潜入中国茶区,足迹遍及安徽黄山、浙江宁波、福建武夷山等著名茶区,详细“了解到何种气候和土壤适于种植优质茶”,并用3年时间“完全掌握了种茶和制茶的知识和技术”。1853-1856年,福钧再次来到中国,掌握了更多种茶知识,并将这些知识传入印度,这为印度茶业诞生和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知识营养和智力支撑。
没有中国种茶知识的传入,也就没有印度茶业的产生与发展。早期的欧洲人包括英国人都幼稚地认为,绿茶与红茶是两种不同的茶树叶子制造的,但经过第一次潜入中国茶乡,福钧就意识到这种说法完全错误。“福钧于1843年奉皇家园林协会之命第一次来华执行采集任务,那次他进入了茶叶种植区的边缘地带,这是整个采集任务中的一部分。那次行动为他带来了一个重大发现:绿茶和红茶其实都来源于一种植物。”[58]“他对中国的第一个三年之旅中所得到的几份茶叶标本进行一番彻底研究之后得出结论:绿茶和红茶那特殊的加工工艺是导致它们之间所有差异的缘由。他的那些植物学同行要过很长时间才能接受这种观点,并要求提供更多的证据。”[59]在福建,他得到了一株活的武夷山红茶产区的茶树,“我后来把这棵茶树带到北方的绿茶产区,在经过细致的对比后,我发现它与绿茶茶树完全相同。也就是说,通常运到英国去的,来自中国北方的那些红茶和绿茶,实际上产自同一茶树树种,它们在颜色、味道等方面的不同,仅仅是因为加工方式的不同而已。”[60]福钧经过多方调查,得出的结论依旧:绿茶与红茶只是加工方法不同,并不是来自不同的茶树。但在中国,生产绿茶与红茶的区域不同,这就容易使人产生误解。1849年5月,他在调查宁波绿茶产区后,又赶赴红茶极品产地武夷山。“尽管正如他已确认的那样,红茶和绿茶的源出系同一种植物,但这两种茶叶永远不会种在同一片地带。”[61]“而第二次中国之旅将使这场争论在福钧手中彻底终结。”[62]由此可见,福钧拥有的茶叶知识的重要性。为了获得更多茶叶知识,他亲自深入茶区,多方观察。他不打自招地说:“这样我不仅可以采集到真正出产最好品质的绿茶的茶树,而且也可以获得一些有关徽州茶区的土壤特性以及栽种方法等信息。”[63]他的茶叶知识是潜入中国、进行长期窥视的结果。
二是茶叶种制技术。印度所有茶业技术都是直接从中国传入的,福钧对中国茶叶种制技术的窃取是一种重要的技术传入途径。1834年,印度茶叶委员会秘书戈登潜入中国,调查栽茶制茶方法,也是一种赤裸裸非法窃取中国茶业技术的活动。印度植茶试验后,由于所采用的是中国的次等茶籽,制茶水平不高,所制茶叶质量并不理想,这说明种茶、制茶技术很重要,东印度公司试图从中国输入。“东印度公司首批试验性种植的茶叶的品质可能算不上极致,然而如果中国极品茶叶的生产工艺和相关实践经验能在印度的茶叶种植园生根发芽,真正的中国本土茶艺专家能对喜马拉雅茶农进行茶叶生产流程培训的话,那么喜马拉雅山茶的缺陷将得到有益的改进。”[64]福钧正是被赋予了这样的使命。对于福钧的企图,中国官员心知肚明,他们坚定地认为,“一个英国人要去探访中国农村,除了看看他喜欢的茶叶是怎么种植的,此外便没有别的什么目的了。”[65]1848年,“潜入中国,在中国人鼻子底下窃取中国的茶叶机密”,被称为“在中国充当英国间谍”的福钧,更是全面系统地盗取了中国的“茶叶机密”。1842-1845年、1848-1851年、1853-1856年,他3次来到中国,深入茶区,通过化装潜入、大量盗取、秘密偷运、招募技工等多种手段将中国茶叶采植技术、红绿茶及花茶制作方法通通学到手,用了长达9年时间,“福钧终于完全掌握了种茶和制茶的知识和技术”,并且“福钧深知他从中国窃取来的这些有近5000年历史的诀窍的价值” [66]后来都被带回印度后,最终的结果是,这极大推动了印度茶叶种植业的向前发展。
1848年10月,他利用欺骗手段取得了一家外销绿茶厂主的同意,全程参观、仔细观察了绿茶生产的全过程,对各个生产环节详加记录,最终掌握了绿茶的生产技术,这实际上就是一次盗取行为。福钧知道:“制茶的配方在这个戒备森严的国家可是机密。”但福钧身着一套官服,谎称自己是来自远方省份、博学而饱受尊敬的官员来视察绿茶厂。工厂主管信以为真。就这样,福钧通过欺骗手段,在工厂主管的带领下,将外销绿茶生产秘密轻松地盗取到手。“在福钧的来华任务中,学到制茶工艺程序无疑与为印度的茶叶种植园搞来一批质地出色的茶叶苗木一样重要。茶叶从摘下到成为可冲泡成品,要经历一个复杂烦琐的生产流程:晒青、炒青、揉捻,如果要加工成红茶的话,还得经历一道发酵程序。”[67]
1849年7月,福钧在著名红茶产区武夷山学会了先进的茶树无性繁殖方法。“幸运的是,大自然赐予了茶农们一种大量收获大红袍的办法。茶叶易于繁殖,只要随便割下一要枝条,移植,弯曲压入土壤,留下的新芽就会很快长成网状根须。这种植株繁殖法叫无性繁殖,即不需要花粉和受精,也就是无性生殖的办法。无性繁殖是一种比播种繁殖更昂贵的方法,但实行无性繁殖可以获得植株母体的直系遗传副本。在农艺学上,这一技术应用了数千年,用以保护那些珍贵罕见的品种。同样,通过无性繁殖而生的大红袍树很快就遍布于整个武夷山区。”[68]他在武夷山还学会了一些茶道的知识,特别是泡茶对水的要求。尤其重要的是,他了解到了使绿茶变成红茶的过程:对茶叶进行发酵处理,从而使茶叶的颜色变暗。绿茶的制作则不经过这道工序[69]。在武夷山的时候,“他记下了茶叶的小型加工、晾晒程序和红茶与绿茶之间的区域性差异。”[70]武夷山是著名红茶的天下,显然,福钧在这里记下的茶叶加工技术,说明他亲自见到了红茶的加工情况。中国祖先经长期实践发明的这一珍贵茶树种繁殖和红茶加工工艺方法,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成了福钧这一茶业经济间谍的囊中之物。
(二)窃取茶籽茶苗茶树
印度茶业的建立和发展与英国长期盗取中国茶籽、茶苗、茶树密不可分。1848年,福钧潜入中国,大肆偷购中国优良茶籽、茶苗输入印度。英印“政府决议以移植中国种为便,又往安徽、杭州、宁波、福建武夷山购觅良种,植于西北诸州。”[71]担当此重要使命的就是福钧。英国驻印总督达尔豪西侯爵命令福钧:“你必须从中国盛产茶叶的地区挑选出最好的茶树和茶树种子,然后由你负责将茶树和茶树种子从中国运送到加尔各答,再从加尔各答运到喜马拉雅山。”[72]福钧来中国的目的十分明确,他只对猎取中国最有名的茶种感兴趣:“从中国的极品茶叶产区弄到极品茶叶可谓意义重大。”“因此他知道他必须亲手查明他要采集的茶树样本的生长位置、所处生态环境,以及种植过程等方面的情况。”他供出了第二次中国之行的企图:“我受光荣的东印度公司之托前往中国,目的在于运送中国最上等的茶种和树苗。”[73]福钧真正做到了死心塌地、不遗余力,他是“一个杰出的植物学家,同时也是一个冒险家”,在宁波地区因以高价为诱饵,“他采集到许多茶种”。1848年12月15日,福钧得意洋洋地致信达尔豪西侯爵:“我高兴地向你报告:我已弄到了大量茶种和茶树苗,我希望能将其完好地送到您手中。在最近两个月里,我已将我收集的很大一部分茶种播种于院子里,目的是不久以后将茶树苗送到印度去。”为尽量减少损失,福钧发往加尔各答的每批茶种和茶苗都是分3只船装运的,但这批茶种和茶树苗到印度后几近全军覆灭,仅只有80棵茶苗存活。嗣后,在武夷山及其他地区,他又搞到大量茶种及茶树苗。1851年3月16日,“福钧和他招聘的工人们乘坐一只满栽茶种和茶树苗的船抵达加尔各答。他们的到来将使喜马拉雅山的一个支脉的山坡上增加两万株茶树”[74]。他说:“1848年秋天,我曾经送了大量茶树种到印度。”[75]后来,他改良了保存种子的方法,装茶苗的柜子安全运达目的地后,当“打开柜子的时候,所有茶树都长得非常好,柜子中一共有不下12833棵茶树,还有很多还处于萌芽阶段。”[76]福钧自己亲自供认:1848年,“在10月份和11月份,我又从徽州和浙江省各地采集了大量茶树种子及幼苗。”“这些茶树,不只是来自舟山金塘岛以及宁波地区,还有来自著名茶区松萝山和武夷山的。”[77]1850年夏天,这些茶树安全抵达加尔各答,状况很好。“为了接收我从宁波附近茶区采获来的另一批树苗,我也离开了上海,前往宁波。”[78]“在采集了大量茶树和树苗后,我于12月底离开了宁波,前往上海。”[79]到达上海后,他发现已经招到一些很好的制茶工,一切都很顺利,比他最乐观的估计还要顺利。福琼为东印度公司搞到了大批茶种、茶苗,难怪他得意忘形地说:“喜马拉雅茶园可以夸口说,他们拥有的茶树树种许多都是来自于中国第一流的茶叶产区——也就是徽州的绿茶产区,以及武夷山的红茶产区。”[80]福钧窃取的中国优良茶种作用巨大,运到目的地后,“这大大促进了印度茶叶种植业的发展。”[81]
(三)秘招茶叶种制技工
印度茶业的起步阶段走过不少弯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缺少茶叶种制技术。为了更好地发展印度茶业,必须尽快聘请到中国茶叶种制技工,“只有他们才熟悉怎么加工茶叶。”[82]1848年,东印度公司又派福钧潜往中国执行“一种经济间谍活动。”英印总督命令福钧,“必须尽一切努力招聘一些有经验的种茶人和茶叶加工者”,这对发展印度茶业不可或缺,“没有他们,我们将无法发展在喜马拉雅山的茶叶生产”,因为“只有中国的种茶者才能把他们的种茶和制茶知识传播给印度的茶叶种植者。”1851年,福钧招聘到8名中国工人,其中6名种茶制茶工人,2名制作茶叶罐工人,他们于3月16日乘船抵达加尔各答。3年后,福钧“完全掌握了种茶和制茶的知识和技术。这甚至对印度的茶叶种植者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要想同中国茶竞争,他们就必须掌握这些知识和技术”。1853-1856年,福钧又到中国活动了3年,“目的是进一步了解花茶的制作技术,招聘更多的中国茶叶工人到印度去帮助东印度公司扩大其茶叶种植规模。”[83]中国茶叶种制技工进入印度传播茶业技术后,印度茶业也从摸索、试验阶段开始转向迅速发展阶段。有人评价说:“他还成功地招募了八名具有很高资历的茶叶专家,并购买了大量的茶叶加工设备。”福钧不但将自己送回印度的茶树移栽成功,“并且由他所招募的中国人生产出了优质的茶叶。”[84]1852年起,印度茶叶开始成为对英国出口的重要货品,该年出口英国23.2万磅,1859年,首次超过百万磅,1869年,又突破千万磅,1886年,竟达7685.5万磅[85]。这当然与中国茶工的辛勤劳动与无私传播茶业技术密不可分。
三、福钧对华茶业经济间谍活动的恶劣影响
福钧的非法茶业经济间谍活动促成了英国殖民地印度、锡兰等地茶业的迅速崛起,对中国而言却完全是一场巨大灾难。“19世纪英国茶叶企业的发展对中国的茶叶产业产生了严重的损害”,“中国的茶叶产量从1886年高峰时期的2.96亿磅降至1920年的4100万磅。”[86]这一极其恶劣的结果归根到底与福钧对华茶叶经济间谍活动的显著效果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一)中国积累的茶业技术完全失密
茶业机密就是数千年来中国古代劳动人民认识、驯化、栽培、采制、管理茶叶的一系列核心知识技术的总和,是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智慧和心血的宝贵结晶。为了保护茶业机密,明清统治者制定了严格的产业政策,禁止茶籽茶苗出境,更不准外国人尤其是西方人任意进入茶区。这种严格保护本国产业安全的政策当然无可厚非,这是一个主权国家生存和发展权利的必然要求。英国要发展茶业,“为此首先必须找到能刺探到中国茶叶生产机密的专家”[87]。虽然英国对茶叶生产一窍不通,但还是通过一系列经济间谍活动,非法获得了发展茶业必需的物质、人才、技术条件。英国深知,福钧从中国窃取来的这些有近5000年历史的茶业技术诀窍价值无比珍贵,表明福钧的冒险行动取得了巨大成功。这种“成功”却是以中国茶业技术完全泄密和英国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为代价的。“福钧从中国成功盗走茶种及其相关技术,制造了迄今为世人所知的最大一起盗窃保护的商业机密的事件。时至今日,福钧的做法仍被定义成商业间谍活动,在人们看来,他的行为的性质就跟偷走了可口可乐的配方一样。”[88]从此,中国茶业技术完全无密可保。正是通过对中国茶业技术的无偿占有、肆意使用和着力发展,19世纪30年代后,英国才有了大力发展殖民地印度茶业的基本条件。19世纪70年代后,在印度茶业发展的基础上,英国再向殖民地锡兰甚至非洲的马拉维、南非、肯尼亚、乌干达等地扩展。英国这个原本对茶毫无所知的国家,正是依靠中国茶业技术作基础,其殖民地茶业迅速发展,并很快压倒中国,成为世界著名产茶地区。
(二)加速了中国茶业的衰败进程
英国人津津有味地自夸道:“只用了短短一代人的时间,印度新生的喜马拉雅茶叶产业,无论在茶叶质量,还是在茶叶产量或是价位上都超过了中国茶叶产业。”[89]英国对中国茶业的赤裸裸经济间谍活动是促使近代中国茶业迅速走向衰败的重要因素。“当中国人意识到福钧从他们手中窃走了一件无价之宝的时候,已经为时太晚,无法挽回他们的损失了。”[90]正是得益于福钧的疯狂茶业经济间谍活动,英国殖民地印度茶业很快就打破了中国垄断世界茶市的局面,加剧了世界茶业的激烈竞争,极大冲击了中国茶业,削弱了中国茶业的核心竞争力,使中国茶叶外销量锐减,国际市场急剧萎缩和不断丧失,茶区走向衰落。在印度、锡兰为代表的英国殖民地茶业强力竞争下,世界茶业格局发生巨变,开启了“洋茶日盛,华茶日衰”[91]不可逆转的局面。
1838年前,印度茶业尚处于试验阶段,产量十分有限。1838年仅产茶12小箱,计480磅。翌年为95箱,1861年达到150万磅[92]。1868年突破1000万磅,为1148万磅,1874年达2113.7万磅,1875年估计为3000万磅[93],分别占中国茶叶出口量的5.59%、9.14%、12.37%[94]。虽然印度茶业发展很快,但世界茶市约90%份额仍为中国占据。1876年起,英国殖民地印度、锡兰茶业发展加快,中国茶业受到严重冲击[95]。
表1、1876-1926年,印度、锡兰、中国茶叶出口数量及占世界茶市比重(单位:千磅)
年代 | 1876年 | 1886年 | 1896年 | 1906年 | 1916年 | 1926年 |
印度销量 | 22500 | 67250 | 138921 | 236090 | 292594 | 359140 |
印度比重% | 7.9 | 15.8 | 25.2 | 34.5 | 33.0 | 40.1 |
锡兰销量 | 0.2 | 3561 | 110096 | 170521 | 203256 | 217184 |
锡兰比重% | 约为0 | 1.3 | 20.0 | 24.9 | 22.9 | 24.2 |
印度锡兰销量 | 22500.2 | 72611 | 249016 | 406611 | 495850 | 576324 |
印度锡兰比重% | 7.9 | 17.1 | 45.2 | 59.4 | 55.9 | 64.3 |
中国销量 | 235025 | 295640 | 228379 | 187217 | 205684 | 111909 |
中国比重% | 82.6 | 69.4 | 41.5 | 27.4 | 23.2 | 12.5 |
世界总销量 | 284521.2 | 425809 | 550400 | 683807 | 885937 | 896068 |
资料来源:据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中华书局,1962年,第181页及吴觉农,范和钧:《中国茶业问题》,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69-171页资料计算整理。
市场丧失是外销不振的必然结果和重要体现。世界茶叶消费市场以英国、美国、俄国、澳洲、加拿大等国为最重要,其中英国是世界最大的茶叶消费市场,也是中国茶叶主市场,最多一年销往英国的茶叶超过百万担,占中国茶叶出口总量70%以上,1874年仍超过60%[96]。但印度茶业兴起后,“英国唯一注视的是印度茶”[97],将之视为本国茶业,千方百计扶助印度茶进入英国,无下限地限制、打击中国茶的销售。由于印度、锡兰等英国殖民地茶的竞争,中国茶销往英国数量及占英国茶市比重迅速下降。1881年,中国茶销往英国达到16450万磅,1897年,仅为3500万磅,印度、锡兰茶叶输往英国数量则由4452.8万磅增至23300万磅。受其影响,印度、锡兰茶在英国茶市中的比重不断上升,中国茶比重不断下降。1865年,印度、锡兰茶占英国茶市比重3%,中国茶占97%。1897年,印度、锡兰茶完全垄断了英国市场,中国茶地位已无足轻重。20世纪后,中国茶基本丧失英国市场。1911年,印度茶占英国茶市57.5%,锡兰占30.25%,两合为87.75%,中国茶仅为5%[98]。其他如美国市场、俄国市场、澳洲市场等茶叶市场,均受到英国殖民地茶猛烈竞争,中国茶在这些市场同样节节败退,全面萎缩[99]。
(三)增加了中国社会民生改善的困难程度
英国窃取中国茶业机密后,大力发展殖民地茶业,与中国茶业展开激烈竞争,中国茶业发展趋势很快发生逆转,茶利不断减少,茶农生活困苦,茶商处境艰难,中国社会民生问题突显[100]。
1、茶叶出口价值升高不久即持续走低。茶叶出口价值折成美元,能够比较准确反映茶叶出口价值的发展情况。高峰出现在19世纪60至70年代,1883年前,年出口价值在4300万美元以上,翌年,开始呈螺旋式下降,1899年,尚有2200余万元,但仅及1872年的35.64%。20世纪以来有所上扬,1900-1905年徘徊在1300余万元-1900余万元间,1906-1917年,除1915年、1916年为3400余万元外,均在2000余万元。1918年,茶叶价值不足1872年的三分之一,翌年,骤增至31133826美元,约为1872年的一半。1922-1929年,出口价值尚有1400万至2600万余美元,相当于1872年的20%-40%,嗣后,剧烈下滑,指数由20%下降到不足1%,个别年代甚至不足0.05%。抗战胜利后,虽有一定回升,但已是日薄西山,回天无力了。综观70余年间,茶叶年出口价值由6000余万美元退至数十万美元,不能不说中国茶叶利源已经枯竭。这当然与英国窃取中国茶业技术,大力发展殖民地茶业造成的强力竞争关系极大。
2、茶叶生产的衰落使茶农生活严重受困。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茶农种茶利益大减,个别年份、个别地区出现亏本现象,生产积极性有所降低,但盈亏情况互见。19世纪80年代后期始,各产区茶农经营环境普遍恶化,亏本加剧,收支状况每况愈下[101]。1887年,福建茶“较昔贱至数倍”[102]。北岭茶价“比前低有大半”,每百斤茶挑进城只能得到七八银元,不够采工的伙食费。有人替厦门茶农算了一笔帐:1887年,每百斤茶价值银11.385两,扣去各种费用,归种茶人所得仅3.529两,占货价31%[103]。1891年,福州因茶叶“逐年见衰象”,竟然发生“其茶圃变为谷田或罂粟园”[104]的极端现象。据汉口茶业公所报告,1887年,茶农茶价“除开销摘工之外实已无余”[105]。皖南茶商连年亏本,不仅造成商贩受累,而且“皖南山户园户亦因之交困”[106]。皖北六安茶区霍山县,茶价自光绪后“愈趋愈下”,茶百斤贵不过钱余,贱至七八分,“以是民用益绌”[107]。茶价跌落造成茶农生活困苦现象广泛存在于各产区,“业茶者亦衰耗矣”[108]。茶业难以维持生计,“有田者归耕,无田者以砍柴为活。叹种茶者,勤劳艰苦,大受茶累矣。”[109]大部分地区的茶农生活都不好过,许多情况下,他们“终岁栽植辛勤,不获一饭之饱。”茶价过低,“除开销摘工之外实已无余。”[110]不仅如此,茶农还要受到茶商、茶贩的种种盘剥,“向之茶农茶工因之辍业,饥寒逼切”[111]在所难免,生活倍受煎熬。
3、茶叶贸易的衰落使茶商经营亏损加剧。19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茶商经营环境日渐恶化,亏损现象愈演愈烈[112]。“开茶行破家败产者不知有几”[113],“凡茶务中人,不惟尽失从前应得大利,且不得不改图别业”[114]就是当时茶商经营状况的真实写照。清廷官吏几乎众口一辞,道出了茶商亏损破产的普遍情况。1887年,闽海关税务司汉南申报告:福建“开茶庄及采箱者,屡年折本,倾家荡产,人多不以茶为正项生理。”[115]1888年,两江总督曾国荃说:“以致华商连年折阅,遐迩周知……营运俱穷,空乏莫补。”[116]19世纪90年代,安徽歙县县令何润生在《茶务条陈》中谈到,皖南茶商“百无一人可沾余润,甚有坐本全亏者。”[117]湖南巡抚卞宝第说:华商“是以连年亏折”[118],1894年,后继巡抚吴大澄说到,在洋商压抑下,茶商“倾家荡产者有之,投河自尽者有之。”[119]1887年,江汉关税务司裴式楷报告:“在贩运商人,血本全糜,多难再举。”[120]此年,汉口的“中国商人损失极重,并且还要继续遭到损失。”[121]嗣后的日子的确更糟。1894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也说:“近年湖北、湖南两省茶商颇多亏累。”[122]江西的情况大同不异,巡抚松寿道:“茶商年年亏折,裹足不前。”[123]整个中国外销茶区正如史料所云,茶商“沾润者不过数千两数百两,且其人有数,而折短者动辄数万两数千两,且其人甚多。”有人甚至总结道:“予足迹半天下,见二十年来,以业茶起家者,十仅一二;以业茶破家者,十有八九。”[124]
总之,“福钧从中国成功盗走茶种及其相关技术,制造了迄今为止世人所知的最大一起盗窃受保护的商业机密的事件。”[125]正是得益于福钧的茶业经济间谍“冒险行动收获巨大”[126]这一客观事实,英国不但很快完全掌握了种茶和制茶知识和技术,最终还使“中国错过了赚钱的机会,再加上19世纪末的经济灾难,中国茶叶生产因此受到了严重打击。”[127]本来独步世界的中国传统优势产业茶业最终却不可挽回地走向了衰落。今天,牢记这一深刻而惨重的历史教训,对改革开放过程中更好发展本国产业,自觉维护国家利益,确保国家经济安全,有效化解潜在风险,促进产业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然也是非常必要的。
[①] 佚名:《谁偷走了中国的茶叶》,《茶报》2002年第3期,第43页。
[②] 佚名:《谁偷走了中国的茶叶》,《茶报》2002年第3期,第43页。佚名:《谁偷走了我们的茶叶》,《参考消息》2002年3月25日,第9,内容相同。
[③](美)萨拉•罗斯:《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孟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8页。
[④] 本书编写组:《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第1047页。
[⑤] 主要成果体现在专著:(美)萨拉•罗斯:《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孟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及介绍性文章《谁偷走了中国的茶叶》(《茶报》2002年第3期,第43-44页)。《谁偷走了我们的茶叶》,《参考消息》2002年3月25日,第9,内容相同。
[⑥] 习近平:《习近平致信祝贺首个“国际茶日”》,《人民日报》2020年5月22日,第1版。
[⑦]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1191页。
[⑧] 孙文:《建国方略》,刘明,沈潜评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95页。
[⑨](荷)乔治•范•德瑞姆:《茶:一片树叶的侍传说与历史》,李萍,谷文国,周瑞春,王巍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573页。
[⑩](美)萨拉•罗斯:《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孟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53页。
[11] 刘鉴唐,张力:《中英关系系年要录》第1卷,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33页。
[12](英)麦克伊文:《中国茶与英国贸易沿革史》,冯国福译,《东方杂志》第10卷第3期,1913年9月,第34页。
[13] 陈椽:《茶业通史》,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第448页。
[14](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叶笃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539页。
[15]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270页。
[16]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512页。
[17](英)麦克伊文:《中国茶与英国贸易沿革史》,冯国福译,《东方杂志》第10卷第3期,1913年9月,第35页。
[18]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270页。
[19] 刘鉴唐,张力:《中英关系系年要录》第1卷,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287页。
[20] 刘鉴唐,张力:《中英关系系年要录》第1卷,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739-742页。
[21](英)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张汇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92页。
[22](英)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康成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3页。
[23]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268页。
[24](英)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康成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3页。
[25]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270页;(英)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康成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3页。
[26](英)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康成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93页。
[27](英)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康成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4页。
[28] 习近平:《共倡开放包容 共促和平发展》,《人民日报》2015年10月23日,第2版。
[29](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叶笃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10-11页。
[30] 佚名:《中外关系史译丛》,朱杰勤译,海洋出版社,1984年,第201-202页。
[31] 刘鉴唐,张力:《中英关系系年要录》第1卷,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740-742页。
[32] 刘鉴唐,张力:《中英关系系年要录》第1卷,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397、第401、第732-733页。
[33] 庄国土:《从丝绸之路到茶叶之路》,《海交史研究》1996年第1期,第10页。
[34](英)罗伯特·福琼:《两访中国茶乡》,敖雪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06页。
[35]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1186页。
[36]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1187-1188页。
[37](美)萨拉·罗斯:《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孟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49-50页。
[38](美)萨拉·罗斯:《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孟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3页。
[39](英)艾伦·麦克法兰,艾丽斯·麦克法兰:《绿色黄金:茶叶帝国》,扈喜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41页。
[40](美)萨拉·罗斯:《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孟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88页。
[41](美)萨拉·罗斯:《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孟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16页。
[42](美)萨拉·罗斯:《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孟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54页。
[43](美)萨拉·罗斯:《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孟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16页。
[44](美)萨拉·罗斯:《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孟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53-54页。
[45](美)萨拉·罗斯:《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孟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54页。
[46](英)罗伯特·福琼:《两访中国茶乡》,敖雪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05页。
[47](英)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康成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页。
[48]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1038页。
[49](美)萨拉·罗斯:《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孟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46-47页。
[50](英)艾伦·麦克法兰,艾丽斯·麦克法兰:《绿色黄金:茶叶帝国》,扈喜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25页。
[51]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1187页。
[52]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中华书局,1962年,第180页。
[53] 佚名:《谁偷走了中国的茶叶》,《茶报》2002年第3期,第43页。
[54](美)萨拉·罗斯:《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孟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16页。
[55](美)萨拉·罗斯:《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孟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86页。
[56](美)萨拉·罗斯:《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孟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89页。
[57](美)萨拉·罗斯:《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孟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88页。
[58](美)萨拉·罗斯:《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孟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21页。
[59](美)萨拉·罗斯:《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孟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22页。
[60](英)罗伯特·福琼:《两访中国茶乡》,敖雪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93页。
[61](美)萨拉·罗斯:《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孟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81页。
[62](美)萨拉·罗斯:《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孟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88页。
[63](英)罗伯特·福琼:《两访中国茶乡》,敖雪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14页。
[64](美)萨拉·罗斯:《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孟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52-53页。
[65](英)罗伯特·福琼:《两访中国茶乡》,敖雪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92页。
[66] 佚名:《谁偷走了中国的茶叶》,《茶报》2002年第3期,第44页。
[67](美)萨拉·罗斯:《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孟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16页。
[68](美)萨拉·罗斯:《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孟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21页。
[69] 佚名:《谁偷走了中国的茶叶》,《茶报》2002年第3期,第44页。
[70](美)萨拉·罗斯:《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孟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23页。
[71]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1186页。
[72] 佚名:《谁偷走了中国的茶叶》,《茶报》2002年第3期,第43页。
[73](美)萨拉•罗斯:《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89-90页。
[74] 佚名:《谁偷走了中国的茶叶》,《茶报》2002年第3期,第44页。
[75](英)罗伯特•福琼:《两访中国茶乡》,敖雪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00页。
[76](英)罗伯特•福琼:《两访中国茶乡》,敖雪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04页。
[77](英)罗伯特•福琼:《两访中国茶乡》,敖雪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92页。
[78](英)罗伯特•福琼:《两访中国茶乡》,敖雪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93页。
[79](英)罗伯特•福琼:《两访中国茶乡》,敖雪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99页。
[80](英)罗伯特·福琼:《两访中国茶乡》,敖雪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93页。
[81] 佚名:《谁偷走了中国的茶叶》,《茶报》2002年第3期,第44页。
[82](英)罗伯特·福琼:《两访中国茶乡》,敖雪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93页。
[83] 佚名:《谁偷走了中国的茶叶》,《茶报》2002年第3期,第44页。
[84](英)罗伊·莫克塞姆:《茶:嗜好、开拓与帝国》,毕小青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111页。
[85]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1193页。
[86](英)罗伊·莫克塞姆:《茶:嗜好、开拓与帝国》,毕小青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212页。
[87] 佚名:《谁偷走了中国的茶叶》,《茶报》2002年第3期,第43页。
[88](美)萨拉·罗斯:《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孟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319页。
[89](美)萨拉·罗斯:《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孟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96页。
[90](美)萨拉·罗斯:《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孟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83页。
[91]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1203页。
[92]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 第1187页。
[93]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1191页。
[94] 吴觉农,范和钧:《中国茶业问题》,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69页。
[95] 详细内容请参陶德臣:《印度茶业的崛起及对中国茶业的影响与打击》,《中国农史》2007年第1期,第66-76页;陶德臣:《英属锡兰茶业经济的崛起及其对中国茶产业的影响与打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4期,第74-88页。
[96] 陶德臣:《清至民国时期茶叶国别市场分析》,《安徽史学》2009年第6期,第16-25页。
[97]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1192页。
[98] 佚名:《英国之茶输出入及其市况》,《工商半月刊》第4卷第12期,1932年6月,第8页。
[99] 详细内容请参陶德臣:《清至民国时期茶叶国别市场分析》,《安徽史学》2009年第6期,第16-25页。
[100] 详细内容请参陶德臣:《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衰落的社会影响》,《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第93-98页。
[101] 陶德臣:《近代中国茶农的经营状况》,《中国农史》2003年第1期,第70-78页。
[102]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448页。
[103]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1464-1465页。
[104]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448页。
[105]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451页。
[106]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451页。
[107]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1582页。
[108]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1473页。
[109]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447页。
[110]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1473页。
[111]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445页。
[112] 陶德臣;《近代中国茶商的经营状况》,《近代中国》2000年第10辑,第69-87页。
[113]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448页。
[114]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中华书局,1962年,第281页。
[115]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447页。
[116]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451页。
[117] 陈祖椝,朱自振:《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农业出版社,1981年,第433-434页。
[118]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975页。
[119]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976页。
[120]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1473页。
[121]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675页。
[122]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976页。
[123]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中华书局,1962年,第186页。
[124]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555页。
[125](美)萨拉•罗斯:《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孟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319页。
[126] 佚名:《谁偷走了中国的茶叶》,《茶报》2002年第3期,第44页。
[127] 佚名:《谁偷走了中国的茶叶》,《茶报》2002年第3期,第44页。

 中国人民大学茶道哲学研究所——致力于茶道哲学学科体系建设
中国人民大学茶道哲学研究所——致力于茶道哲学学科体系建设